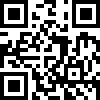明朝永乐年间,江苏地界有个书生,名叫赵吏。这赵吏读书很是用功,可惜天不从人愿,连续几年科举都没有考中,他眼看年纪大了,不由得心灰意冷,便决定放弃功名,纵情山水。

早年间,赵吏家中颇有资财,能让他衣食无忧。因此,他只背了个书囊,就四处游历,希望增长见识。
这一日,赵吏到一个名叫白杨镇的小镇上歇脚。大清早的,他便向掌柜的打听道:“掌柜的,附近有没有什么知名的景色,能够供游人玩赏的?”
那掌柜的想了想道:“咱们这是个小镇,平时也没什么游人,如果说景色的话,西边的碧鸡山上有个凉亭,日出之时在那里登高望远,能够一览山脚全镇子的景象。”
赵吏听了,也是颇为感兴趣,心想:“那些素有盛名的景色,我也走过了好些,也没有多大意思,或许这荒山野岭的景色,反而别有一番野趣。”
于是,他就收拾好行囊,往西边的碧鸡山走去。出了镇子,还要走上一段野路,经过一个小山村,才能到达山脚。赵吏在田野里走了大半天,到了傍晚时分,他见到一个牵着牛的老道士迎面走来。

这老道士蓬头垢面,衣服都乱糟糟的,还挽着裤脚,倒像个农民一样。赵吏见他有趣,便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那老道士也看了看他,忽然出声道:“小伙子,贫道看你有血光之灾啊!”
赵吏一听,笑道:“怎么,放牛的老道也会算命吗?”老道士吹胡子瞪眼,道:“你这小伙子,贫道好心提醒你,你却不信!过上几日,你自己就知道了。”
说完,老道不忿地走了。赵吏平时游历四方,也见过不少靠算命为生,满嘴胡言乱语的道士,也没有放在心上。他在小山村中歇了一晚,第二日便独自上山。
这碧鸡山平时没什么游人,山高林密。由于在林中走迷了路,耽搁了好些时间,直到这天傍晚,赵吏还没有爬到山顶。
眼见得天快要黑了,得马上找个借宿的地方。正在这时,他忽然发现前面有座破庙,便急忙赶了过去,心里想道:“破庙就破庙吧,虽然寒酸了些,好歹也有片瓦遮头。”

赵吏走进破庙,只见庙中佛像倾倒,案上的供品早就发霉了,四处都落满了灰,还结了蛛网。正在他四处探看的时候,有个老和尚无声无息地走了出来,把他吓了一跳。
“这位高僧,小生偶然路过此地,如今天色已晚,小生能否在此借宿一晚?”赵吏连忙对那老和尚行礼道。那老和尚没有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,拿起了墙角的扫帚,就离开了。
赵吏觉得他行为颇为古怪,又心道:“算了,一个人住在这荒山野岭,不和人打交道,性情古怪也是正常的。”这么想着,他跟随着老和尚的脚步,发现庙后面还有几间空屋,都没有上锁。
于是,赵吏一个个开门检查,这一看不得了,竟在其中一间房里,发现了一抬黑漆漆的棺材。这棺材被暗红的墨线缠住,跟这破落的庙宇相比,显然有一股十分阴森的味道。
赵吏虽然不信鬼神,但也不想跟棺材同住一屋,只是他再看其他房间的时候,却到处都是荒草和蛇虫鼠蚁,地面还潮湿得很,根本不能住人。只有这停棺材的房间,不仅有床榻,还打扫得十分干净。
“算了,算了,百无禁忌!”赵吏只得如此安慰自己,就在屋中歇下。

虽然这样想,但他他夜里仍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,脑海中总胡思乱想着:“这荒山野岭,深更半夜,若是有什么鬼怪现身,就不妙了。”
到了三更时分,赵吏听到外头有脚步声,正朝着这间屋子走来。他不由得感到有些害怕,便起身走到了窗边,躲在了帘幕之后。
只见房门被轻轻地推开,竟然是白日里见到的那老和尚,手中还提着一盏白灯笼。赵吏松了一口气,心想:“这老和尚,难道是来看我有没有睡好?没想到他看着性情古怪,心地却挺善良。”
说着,他就想要说话,嘴却忽然被人捂住,有个人在他耳边低声道:“别出声!”赵吏转头一看,却见是白天遇到的放牛老道,不知何时已从窗户翻了进来。
见老道满脸严肃神色,赵吏也察觉到了什么,再看那老和尚,手中提着的白纸灯笼很是眼熟,分明就是死人才用的长明灯!

只见老和尚在屋中,慢悠悠地转了一圈,动作很是僵硬,灯光下他面色发青,双眼紧闭,根本不像个活人。他没有发现赵吏二人,半晌后才又慢慢地离开了。
待老和尚走后,赵吏松了一口气,对那放牛老道的称呼也改变了:“道长,这是怎么回事?”那老道士道:“唉!那老和尚原本是这破庙的僧人,后来因作恶多端,被县里斩了首,怕他死后怨气太重化为恶鬼,便将他的棺材停在这里。
死后,他也没有去投胎,而是在此处徘徊,提着白灯笼,意图谋害过路的旅人。不过,有了贫道的法术加护,只要你不要出声,他便发现不了你。”
赵吏听了后怕不已,连忙谢过那老道士。老道士摆摆手道:“我也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善事,倒是你,我看你有些文曲星的命,为何不去科举,反而四处闲逛?”
赵吏便将自己屡试不中的经历,说了出来,老道士却道:“那是你缘分还没有到,若是缘分到了,自然就会中了!”天亮后,赵吏辞别了老道士,回到了家中,开始安心备考。

说来也怪,这一年科举,赵吏真的高中三甲,后来还当上了大官。他还惦记着这段经历,特地找了几位高僧,前去破庙将那老和尚超度,随后将棺材下葬。从此,再也没有过路的旅人被害了。